老街要拆了。消息传下来的时候,整个胡同都嗡嗡响,像捅了马蜂窝。我蹲在自家门槛上,心里头空落落的,也说不上来为啥,就是觉着有啥东西被生生从日子里扯走了,疼倒不疼,就是空得慌。
对门李奶奶颠着小脚过来,嘴里念叨:“留不住喽,啥都留不住。”她眼神往胡同最里头那老院子瞟了瞟,“连那院子带里头的人,都得没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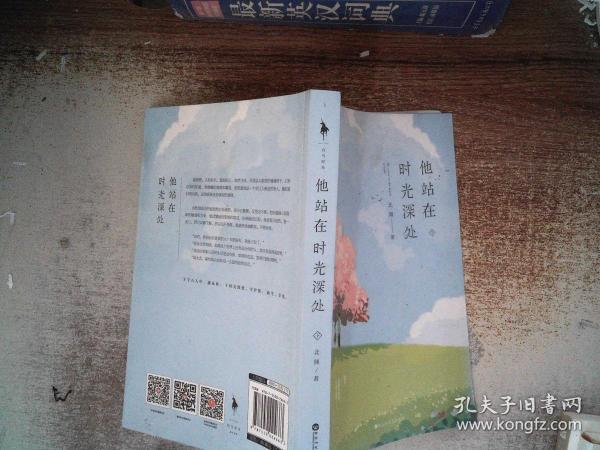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她说的“里头的人”,不是真住着的人。打小我就知道,胡同尽头那栋早就没人住的青砖院儿,有个说法。老人们讲,偶尔天擦黑或者起大雾的清晨,能瞧见个人影,就立在院当中那棵老槐树下头,侧着身,微微朝北边歪着点儿,像在等啥,又像只是在那儿待着,待了老些年。
我们这帮孩子过去忒怕那地方,叫它“鬼院”。有一回和邻居二胖打赌输了,我硬着头皮扒着门缝往里瞅。那是傍晚,天光半明半暗,院子里荒草快有半人高。我就真的看见了——老槐树下,真有个淡淡的影子,穿着不像现在的衣裳,身姿挺拔,却又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孤单。他侧着脸,朝着北边屋顶的方向,一动不动。当时吓得我魂飞魄散,屁滚尿流地跑了,发了好几天烧。打那儿起,我认定,他站在时光深处北倾,是个不得安息的魂儿,带着老辈人嘴里说不清的冤屈或是执念。

后来长大了,念了书,走了不少地方,渐渐忘了胡同里的事儿。直到拆迁的挖掘机轰隆隆开进来,我才猛然想起那个影子。心里头那点空落,忽然就找到了源头。我最后一次翻过那堵快塌的矮墙,进了院子。
院子里比记忆里更破败。我在老槐树根附近,踢开碎砖烂瓦,想着找找有没有老物件能留个念想。结果,真让我在树根一块松动的石板下,摸出个生锈的铁盒子。打开,里头是一沓发黄的信纸,还有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个穿学生装的年轻男子,站在槐树下,笑得明朗,背景就是这院子当年齐整的模样。信纸上的字迹俊秀,是写给他那位因战乱北上求学、却再也没能回来的恋人的。最后一封信没写完,只有半句:“你若归来,无论风雨,我必在此等候。你看,我总站在老地方,朝着你离开的北边,怕你回来时认不出方向……”
信纸在我手里簌簌地抖。我抬起头,夕阳的余晖正斜斜地穿过破败的屋檐,洒在老槐树下。那一刻,我忽然全明白了。哪里有什么鬼魂冤屈。那是一个用尽一生去等待和守望的姿势。他站在时光深处北倾,不是一个恐怖的传说,而是一个人将全部的眷恋与方向,都凝固成了岁月里一个沉默的坐标。 他等的或许永远没回来,可他等的那个动作本身,成了比砖瓦更结实的东西。
拆旧房的巨响从胡同口一路逼近。我捏着铁盒子,心里头那股空落,忽然被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填满了。我们慌慌张张地往前奔,总嫌日子不够新,东西不够潮。可这个快被推平的老院里,却藏着一段比水泥钢筋结实千万倍的情意。他站在时光深处北倾,这姿势本身,就是对易碎流年最温柔的反抗。 他不是困在过去的鬼,他是立在时光河床上的礁石,告诉我们,有些东西,大水冲不走。
我拿着盒子离开时,回头最后看了一眼。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暖金色,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恍惚间,树下似乎依然立着那个清瘦挺拔的身影,依旧微微向北。但他脸上好像不是愁苦,而是一种平静的笃定。
挖掘机的轰鸣已在隔壁响起。明天,这里将是一片废墟,而后是崭新的楼盘。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拆不掉。就像此刻我心里那份沉甸甸的明了——在这个啥都讲究更快、更迭的时代里,我们怕落伍,怕被抛下,慌得脚跟都不沾地。可这个“鬼故事”却幽幽地告诉你:慢一点,深一点,甚至执拗地“停”一点,也许才能守住心里头真正怕丢的东西。他站在时光深处北倾,最终留给我的,不是怀旧的伤感,而是一点面对纷繁世事的定力。 这大概就是老街、老院、老故事,在彻底消失前,能给我的最后一点礼物吧。